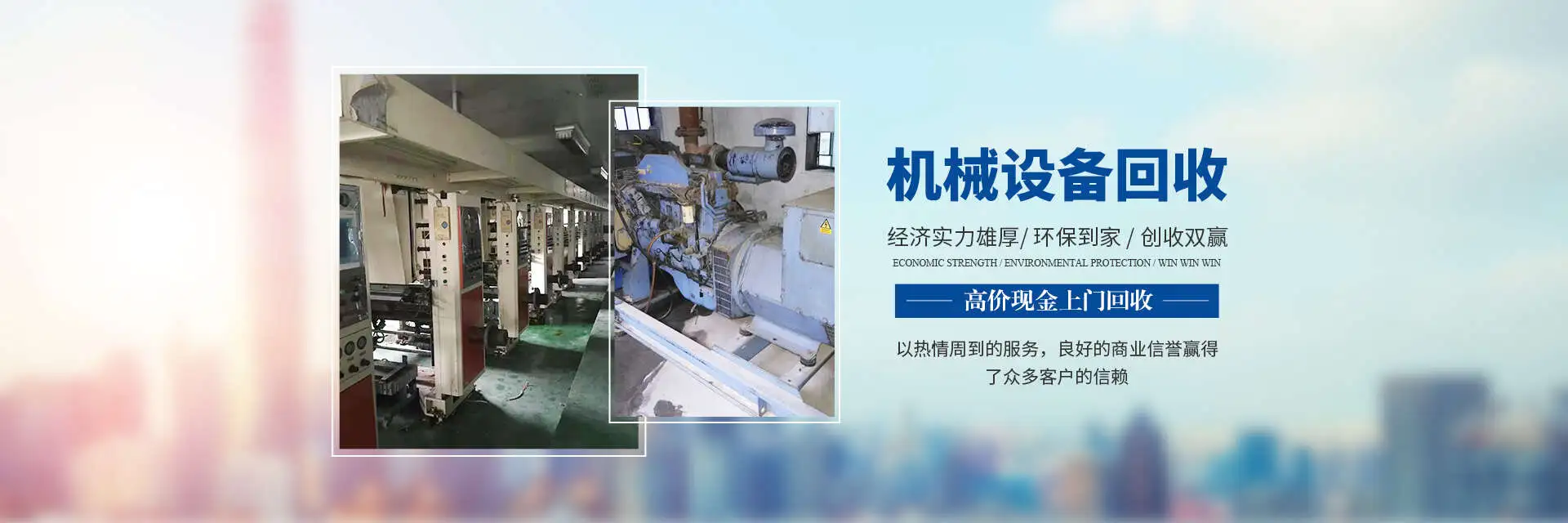为什么垃圾分类在中国难推广?
我国从2000年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制度,16年间各地政府做出过各种尝试,但是垃圾分类制度始终无法大范围推行,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环境问题一直如芒在背,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见的是雾霾,但还有更多看不见却又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比如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是全球性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被不断制造出来,为了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大量的垃圾被运往城乡集合部,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根据住建部2013年的数据,我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垃圾堆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王久良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围城》,通过对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调查,用镜头记录了北京的垃圾围城现象。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垃圾处理厂资料来源:现代摄影网)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垃圾转运站资料 来源:现代摄影网)
面对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垃圾分类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步骤。2016年9月,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将“分类回收,促进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教授杜欢政认为,要消除垃圾围城的隐患,首先要从改变公众观念做起,特别是要推进垃圾分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蓝蔚青也认为政府部门要通过顶层设计让全民参与处置垃圾。
垃圾分类:起步早,走得慢
其实垃圾分类这一步,早在16年前就已经迈了出去。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了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这几个城市针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早在1996年,北京西城区的大乘巷就开始了垃圾分类。居住在大乘巷的一位退休教师王廷韫在一次讲座中认识了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创始人廖晓义,了解到后者恰好想找一个小区做垃圾分类的试点。随后,这件事得到了大乘巷家委会主任陈淑芬的支持,于是家委会一方面通过办讲座、公开信等形式让居民了解并自愿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另一方面利用办公经费买了6个大桶,贴上不同的标识,开始了垃圾分类的尝试。虽然起初居民并不理解,但是在家委会的耐心工作下,居民逐渐接受并习惯了这种新的垃圾模式。
“这样做了一年多以后,居民就逐渐形成了习惯。一些搬迁到别的小区的住户还反映,到了新小区以后不实行垃圾分类,让他们感到像缺了点什么似的不适应。”
2010年的跟踪报道显示,大乘巷有9成的居民自觉参与了垃圾分类。向新住户科普垃圾分类方法已经成了老住户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栋楼的楼门长还自愿承担了垃圾分类的劝导工作,即便租户更迭频繁,垃圾分类的规矩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北京市东城区大乘巷资料 来源:北京日报)
但是垃圾分类在北京却并没有如预想般走上正轨。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深入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调研后发现虽然试点小区数量不断增加,垃圾分类的硬件设备越发完善,占据垃圾总量超过一半的厨余垃圾也得到了更有效的处理,但总体情况仍然不乐观。一方面,试点小区虽然设立了三类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由于市政环卫部门只负责回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完全处于“弃养”状态。
另一方面,居民的分拣意识不足,垃圾分类主要是靠“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二次分拣。原本是承担指导和监督角色的分类指导员,无形中变成了垃圾分拣者,长此以往,其他居民“搭便车”的心理也会越来越严重,垃圾分类制度容易陷入形同虚设的困境。试点小区尚且如此,其他小区的情况恐怕会更糟糕。
上海则在垃圾分类的类别上面进行了好几轮的尝试,1995年开始,先按照“有机”和“无机”的方式进行试点,2008年又实行四色垃圾桶,分别对应“玻璃”,“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调查显示,四分法收集的垃圾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5%。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上海又将“四分法”简化为“厨余果皮”和“其他垃圾”的“干湿两分法”。但是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年发布的居民社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仅有6.5%的居民表示“完全实行了垃圾分类”,而高达32.1%的居民则“从未实行过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为何屡战屡败
垃圾分类遭遇滑铁卢的原因众说纷纭,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原因。其一,居民个体的内在因素,包括对垃圾分类知识掌握程度低,对垃圾分类抱有抵触态度等。其二,垃圾分类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报道显示很多地区虽然居民预先做好了分类,但是市政部门回收时却依然将垃圾合并处理,“一锅化”的后期处理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垃圾分类制度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前期的分类,造成恶性循环。其三,垃圾分类的配套制度不完善,比如奖惩制度,相关的宣传制度等。
但仅此而已吗?以上提到的这三类原因,在推广垃圾分类制度的十几年间,不同的城市针对每一项都出台过专门的举措。居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尚未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我们从娃娃抓起,上海专门举办了中小学生“垃圾分类与减量”网络知识竞赛,“垃圾分类演讲比赛”。
垃圾分类后期处理有缺陷?南宁市制定分别回收处理政策,可回收垃圾由居民或物业公司集中收储后出售给废品收购站,其他垃圾由环卫部门回收再运到垃圾中转处理厂,厨余垃圾则由餐厨公司收集后运往餐厨无害化处理厂。深圳市城管局则表示居民如果发现垃圾混合收运的现象可以拨打专门的投诉电话。
垃圾分类配套制度不完善?事实上,“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早已上马。一方面,北京、上海近期纷纷表示要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另一方面,奖励制度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北京推广智能垃圾回收机,扔垃圾可获积分为公交卡充值,上海推行绿色账号,只要到小区指定地点准确分类投放垃圾账号内就自动存入积分,积分能够兑换各种礼品。然而,垃圾分类制度依然没有成功。
重新审视这三个原因不难发现,这些原因都是从垃圾分类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总结而来,而各地方的解法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垃圾分类制度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经济飞速发展产生的种种环境问题。那么回归到垃圾分类制度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中,似乎能获得一些启示。所以不妨来看看被公认为垃圾分类最成功的日本,是如何把这一制度推向成功的。
日本的成功:公众的觉醒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面临过和中国一样的环境困境,经济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盛行,也造成了垃圾围城的现象。最初日本对垃圾也采取填埋处理,但是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快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环境公害事件如著名的水俣病事件。随后政府改为焚烧处理,但深受环境公害之苦的居民因此展开了全国性的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产生的抵触情绪和行为)。
到了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催生的消费热潮导致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在这个阶段,政府不再是垃圾处理的唯一主导者,广大的居民开始加入到完善垃圾处理制度的过程中。刚开始,居民还只是怀着邻避情绪消极的抵抗。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中部的工业重镇名古屋为了平衡日益增长的垃圾量和土地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计划在藤前海滩湿地建设新的垃圾填埋场,但是这一规划在环境影响评估的过程中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对,不得不中止。
这次的事件促使名古屋政府改变了垃圾管理政策的思路,从废弃物的末端处理转变为“减量化,再使用,循环”(Reduce,Reuse,Recycle)的3R政策。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环境影响评估评估进程,公众开始意识到制造越多的垃圾,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垃圾处理厂要被建设在自家门口。当人们跳出邻避情绪开始理性的看待垃圾处理的问题时,终于发现自己也垃圾处理困境的症结之一。
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吕维霞在2014年底针对日本高校学生及在职员工进行的垃圾分类实证调查分析也显示,33.1%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全民参与,而参与垃圾分类回收最主要的两个动因是公民责任(41%)和社会风气(37%)。当日本面临垃圾处理的难题时,是公众的觉醒和参与最终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公众参与如何实现
公民责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产物,社会风气也不是一天养成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两者都是在公众参与社会议题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填鸭式的政策灌输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所以重点在于“参与”,让公众参与到垃圾处理议题,甚至环境议题当中。
公众对于环境议题的参与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通过特定的制度进行参与,通过抗议等强硬方式参与。最有效的制度型参与就是环境影响评估制度(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简称环评),环评旨在评估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抗议型参与指的是通过聚众表达意见的群体性事件等方式反对一项被认为有害的工程项目,比如今年发生在湖北仙桃,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厂的公众游行事件。
从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抗议型参与并没有摆脱邻避运动的窠臼,被一个地方赶走的项目可能会落户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垃圾总量还在增加,这种垃圾处理的项目就不会消失。而原本能让公众有效参与到环境决策当中,进而提升公民意识和责任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在中国却并没得到充分的发展。
环评在我国虽然开始的很早,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实施,但是主要依靠的却并不是公众,而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审查,必要时会邀请专家,普通民众基本没有机会参与到具体的决策中。虽然2003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有诸如“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条款。但是除了这种原则性条款,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在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序、救济方法等具体事项方面却鲜有规定。
今天,我们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其中的一些比如垃圾处理问题必须要得到公众的参与才能解决。这种时候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反思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的不足,的确,在大乘巷的故事中,居民的自主性和责任感是垃圾分类能有效延续十几年的根本原因。但是,大乘巷的例子注定只能是个例。因为公民意识和责任感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民众们需要充分的了解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更需要有机会参与到这些议题的决策当中。只有当民众有机会成为公民时,我们才能继续讨论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社会学家马歇尔将公民身份拆解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三个方面,这三种权利就是培育公民的土壤,而这个土壤的养护,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环境问题一直如芒在背,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见的是雾霾,但还有更多看不见却又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比如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是全球性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被不断制造出来,为了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大量的垃圾被运往城乡集合部,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根据住建部2013年的数据,我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垃圾堆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王久良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围城》,通过对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调查,用镜头记录了北京的垃圾围城现象。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垃圾处理厂资料来源:现代摄影网)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垃圾转运站资料 来源:现代摄影网)
面对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垃圾分类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步骤。2016年9月,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将“分类回收,促进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教授杜欢政认为,要消除垃圾围城的隐患,首先要从改变公众观念做起,特别是要推进垃圾分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蓝蔚青也认为政府部门要通过顶层设计让全民参与处置垃圾。
垃圾分类:起步早,走得慢
其实垃圾分类这一步,早在16年前就已经迈了出去。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了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这几个城市针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早在1996年,北京西城区的大乘巷就开始了垃圾分类。居住在大乘巷的一位退休教师王廷韫在一次讲座中认识了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创始人廖晓义,了解到后者恰好想找一个小区做垃圾分类的试点。随后,这件事得到了大乘巷家委会主任陈淑芬的支持,于是家委会一方面通过办讲座、公开信等形式让居民了解并自愿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另一方面利用办公经费买了6个大桶,贴上不同的标识,开始了垃圾分类的尝试。虽然起初居民并不理解,但是在家委会的耐心工作下,居民逐渐接受并习惯了这种新的垃圾模式。
“这样做了一年多以后,居民就逐渐形成了习惯。一些搬迁到别的小区的住户还反映,到了新小区以后不实行垃圾分类,让他们感到像缺了点什么似的不适应。”
2010年的跟踪报道显示,大乘巷有9成的居民自觉参与了垃圾分类。向新住户科普垃圾分类方法已经成了老住户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栋楼的楼门长还自愿承担了垃圾分类的劝导工作,即便租户更迭频繁,垃圾分类的规矩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北京市东城区大乘巷资料 来源:北京日报)
但是垃圾分类在北京却并没有如预想般走上正轨。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深入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调研后发现虽然试点小区数量不断增加,垃圾分类的硬件设备越发完善,占据垃圾总量超过一半的厨余垃圾也得到了更有效的处理,但总体情况仍然不乐观。一方面,试点小区虽然设立了三类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由于市政环卫部门只负责回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完全处于“弃养”状态。
另一方面,居民的分拣意识不足,垃圾分类主要是靠“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二次分拣。原本是承担指导和监督角色的分类指导员,无形中变成了垃圾分拣者,长此以往,其他居民“搭便车”的心理也会越来越严重,垃圾分类制度容易陷入形同虚设的困境。试点小区尚且如此,其他小区的情况恐怕会更糟糕。
上海则在垃圾分类的类别上面进行了好几轮的尝试,1995年开始,先按照“有机”和“无机”的方式进行试点,2008年又实行四色垃圾桶,分别对应“玻璃”,“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调查显示,四分法收集的垃圾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5%。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上海又将“四分法”简化为“厨余果皮”和“其他垃圾”的“干湿两分法”。但是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年发布的居民社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仅有6.5%的居民表示“完全实行了垃圾分类”,而高达32.1%的居民则“从未实行过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为何屡战屡败
垃圾分类遭遇滑铁卢的原因众说纷纭,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原因。其一,居民个体的内在因素,包括对垃圾分类知识掌握程度低,对垃圾分类抱有抵触态度等。其二,垃圾分类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报道显示很多地区虽然居民预先做好了分类,但是市政部门回收时却依然将垃圾合并处理,“一锅化”的后期处理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垃圾分类制度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前期的分类,造成恶性循环。其三,垃圾分类的配套制度不完善,比如奖惩制度,相关的宣传制度等。
但仅此而已吗?以上提到的这三类原因,在推广垃圾分类制度的十几年间,不同的城市针对每一项都出台过专门的举措。居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尚未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我们从娃娃抓起,上海专门举办了中小学生“垃圾分类与减量”网络知识竞赛,“垃圾分类演讲比赛”。
垃圾分类后期处理有缺陷?南宁市制定分别回收处理政策,可回收垃圾由居民或物业公司集中收储后出售给废品收购站,其他垃圾由环卫部门回收再运到垃圾中转处理厂,厨余垃圾则由餐厨公司收集后运往餐厨无害化处理厂。深圳市城管局则表示居民如果发现垃圾混合收运的现象可以拨打专门的投诉电话。
垃圾分类配套制度不完善?事实上,“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早已上马。一方面,北京、上海近期纷纷表示要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另一方面,奖励制度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北京推广智能垃圾回收机,扔垃圾可获积分为公交卡充值,上海推行绿色账号,只要到小区指定地点准确分类投放垃圾账号内就自动存入积分,积分能够兑换各种礼品。然而,垃圾分类制度依然没有成功。
重新审视这三个原因不难发现,这些原因都是从垃圾分类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总结而来,而各地方的解法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垃圾分类制度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经济飞速发展产生的种种环境问题。那么回归到垃圾分类制度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中,似乎能获得一些启示。所以不妨来看看被公认为垃圾分类最成功的日本,是如何把这一制度推向成功的。
日本的成功:公众的觉醒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面临过和中国一样的环境困境,经济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盛行,也造成了垃圾围城的现象。最初日本对垃圾也采取填埋处理,但是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快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环境公害事件如著名的水俣病事件。随后政府改为焚烧处理,但深受环境公害之苦的居民因此展开了全国性的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产生的抵触情绪和行为)。
到了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催生的消费热潮导致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在这个阶段,政府不再是垃圾处理的唯一主导者,广大的居民开始加入到完善垃圾处理制度的过程中。刚开始,居民还只是怀着邻避情绪消极的抵抗。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中部的工业重镇名古屋为了平衡日益增长的垃圾量和土地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计划在藤前海滩湿地建设新的垃圾填埋场,但是这一规划在环境影响评估的过程中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对,不得不中止。
这次的事件促使名古屋政府改变了垃圾管理政策的思路,从废弃物的末端处理转变为“减量化,再使用,循环”(Reduce,Reuse,Recycle)的3R政策。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环境影响评估评估进程,公众开始意识到制造越多的垃圾,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垃圾处理厂要被建设在自家门口。当人们跳出邻避情绪开始理性的看待垃圾处理的问题时,终于发现自己也垃圾处理困境的症结之一。
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吕维霞在2014年底针对日本高校学生及在职员工进行的垃圾分类实证调查分析也显示,33.1%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全民参与,而参与垃圾分类回收最主要的两个动因是公民责任(41%)和社会风气(37%)。当日本面临垃圾处理的难题时,是公众的觉醒和参与最终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公众参与如何实现
公民责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产物,社会风气也不是一天养成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两者都是在公众参与社会议题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填鸭式的政策灌输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所以重点在于“参与”,让公众参与到垃圾处理议题,甚至环境议题当中。
公众对于环境议题的参与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通过特定的制度进行参与,通过抗议等强硬方式参与。最有效的制度型参与就是环境影响评估制度(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简称环评),环评旨在评估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抗议型参与指的是通过聚众表达意见的群体性事件等方式反对一项被认为有害的工程项目,比如今年发生在湖北仙桃,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厂的公众游行事件。
从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抗议型参与并没有摆脱邻避运动的窠臼,被一个地方赶走的项目可能会落户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垃圾总量还在增加,这种垃圾处理的项目就不会消失。而原本能让公众有效参与到环境决策当中,进而提升公民意识和责任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在中国却并没得到充分的发展。
环评在我国虽然开始的很早,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实施,但是主要依靠的却并不是公众,而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审查,必要时会邀请专家,普通民众基本没有机会参与到具体的决策中。虽然2003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有诸如“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条款。但是除了这种原则性条款,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在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序、救济方法等具体事项方面却鲜有规定。
今天,我们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其中的一些比如垃圾处理问题必须要得到公众的参与才能解决。这种时候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反思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的不足,的确,在大乘巷的故事中,居民的自主性和责任感是垃圾分类能有效延续十几年的根本原因。但是,大乘巷的例子注定只能是个例。因为公民意识和责任感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民众们需要充分的了解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更需要有机会参与到这些议题的决策当中。只有当民众有机会成为公民时,我们才能继续讨论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社会学家马歇尔将公民身份拆解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三个方面,这三种权利就是培育公民的土壤,而这个土壤的养护,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